作者:王纲 来源:源来渭源
发布/更新时间:2020-09-29 15:3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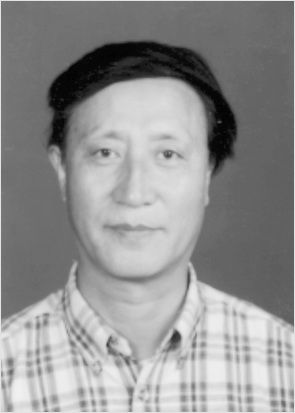
李云鹏,1937年生于渭水源头之五竹镇。曾有一段军旅生涯,此后从事最长的职业是文学杂志编辑,曾任《飞天》文学月刊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忧郁的波斯菊》《三行》《零点,与壁钟对话》《西部没有望夫石》《篁村诗草》等诗集,长篇叙事诗《牧童宝笛》《进军号》《血写的证书》《凌霜花》等,及散文随笔集《剪影,或者三叶草》等。
一盂之水
——渭水源寄情
李云鹏
故乡于我其实是陌生的。许多乡人口上唱得很响的“景”,我竟是从未到过。比如前些年一位南方文士到过且夸说“绝胜江南风光”的天井峡,便是我艳羡很久,至今犹未涉足的梦。少年时就离开故乡的一个乡下孩子,童年的活动天地就只那浅陋的乡街村巷,及蟋蟀和蝈蝈们自由演唱的场园。最遥远的壮游是距家30里的小县城——外乡人奚落的“碟子城”。此外就是到距县城5里、须翻座小山的外婆家。天地就如此宽。而为生计所迫,不足14岁就远别乡土,故乡于我能不陌生吗!
这陌生却无碍我对乡土的自豪。我生身的黑土地,我的至今贫瘠的黑土地,孕生了一条在中国应是小有名气的渭河——那姜子牙以“愿者上钩”悠悠然垂钓的渭河;那成就了一条成语(泾渭分明)的渭河;那滋育了秦陇大地的渭河;那行至潼关渡便义无反顾地扑入黄河,一下子挤宽了、喂粗了黄河的渭河。且我想,在不拒涓细的大海的公民册上,醒目处,定必有我的渭河。
但40岁前的我,竟没有到过距县城仅只20华里的渭水发源地鸟鼠山,竟无缘一览鸟鼠同穴的景观,也无由掬一捧品字泉的水吐抒乡情,也因此,我是确乎想象不来渭河的母地母水的丰歉与清浊的。
在未到鸟鼠山前,渭河在我眼里很大很大,童年那时尤其大,大到可似包容我眼里的整个世界。我们光着屁股的多次冒险泅渡,引来除狼狈吃水之外的大人们的巴掌的严厉警告——渭水可不是你小不点儿们随意耍弄的呵!这也不假。在我七八岁时,我亲见邻家一个长我十岁的大哥哥从河桥上滑落后再没有唤醒的惨景。
在我所知的范围内,第一个把我心目中很大的渭河压进小小一盂的,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顾先生1939年在渭源考察教育时,以一幅题联,给渭源教育界留下了一个学者恒久的精诚——
政海正翻澜渭水鱼龙争变化
树人诚大计门前桃李好栽培
且将足迹印在了渭源的丽山秀水,并吟出了另一幅有名的题联——
疑问鼠山名试为答案歧千古
长流渭川水溯到源头只一盂
那是顾先生访游渭水发源地鸟鼠山后的书感。据说先生那时是骑着毛驴(或说骡子)抵品字泉的。他当时在那孕生了渭河的小泉旁必定感慨多多,惜已无考。但这幅题联传下来了
——它一直活在我中学时的老师、创办了渭源第一所中学的德高望重的张嘉民先生的口上。张嘉民当年请来了顾先生,且陪了顾先生同游鸟鼠山。当我从嘉民先生口里讨来这阙佳联时,渭源土生的我,竞还未到过渭水源头。对顾先生的“只一盂”说,初始我还很有些不愿信服。就想,顾颉刚先生是见过海之大的人,比海小的必是他眼中的“一盂”了吧?我固执地不愿面对源自故乡的有名的渭河只出于“一盂”的评说。这倒促成了我一次匆匆的鸟鼠山之行。
到得鸟鼠山,始信久萦于怀的我的渭水源头的品字泉,那昔年祈雨的乡民们说是绝对灵异因而叩拜年年的龙之湫,确乎仅为“一盂”而已。面对源头小小一泉,已很经了些世事的我,便一切释然,便不再羞“小”,反倒增了些庄重。我记起也是张嘉民先生向我口传的一位三十年代初在渭源县令任上的四川人为渭地渭河书写的另一幅美联,那是县令呼唤在省城学成的嘉民先生返回故土,而在信中寄说的一片殷殷之情——
莫道地贫,有满山白薇供吾一饱
谁云渭浊,看源头活水照人双睛
上联含“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隐居地的渭源南乡首阳山,那里独产白薇;下联含地处渭北的鸟鼠山品字泉,有驳“渭浊”之意——源头活水是可照人双睛的!已去过品字泉的我可以作证,这绝不是溢美之辞,那泉水真真是清可鉴人,绝无杂质的纯清。我也因此不服了那条“泾清渭浊”的成语的判定,我源头的渭水是绝不浊的。这里不存在乡土观念酵生的偏护,而是清亮亮的事实,是凡到过渭水源的人的清亮亮的认定。
[1] [2] 下一页